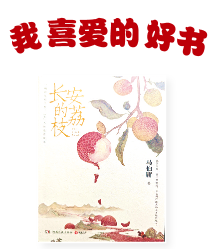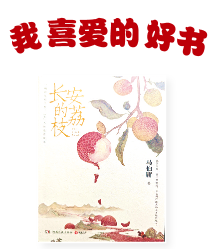王莘迪
周末,家中老人买回来许多新鲜荔枝。爷爷一边给孙女剥着荔枝,一边给她上古诗课,是苏轼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是杜牧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……祖孙两人其乐融融。
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,让我想到一本刚读完没多久的书——马伯庸的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书中的主角叫作李善德,任上林署监事一职,就是给皇家采购蔬菜瓜果的一个小官。在同僚的欺瞒之下担任了“荔枝使”,被迫接下一个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“死亡”任务,荔枝不易保存,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,山水迢迢,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整本书就围绕这个“不可能”,书写了主角如何克服万难,不计成本、不惜代价,成功运回新鲜荔枝的过程。书中描绘的众生相着实精彩,有全力以赴干事的,有伸腿使绊子的,有等着摘果子的……等主角做成了这件壮举,非但没有功劳,还因此获罪,让人唏嘘不已。
小说中最令人震撼的,并非荔枝转运工程本身的艰难,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对“不可能”的习以为常。各级官吏娴熟地调配着人力物力,仿佛用民脂民膏浇灌皇家享乐之树,是再自然不过的流程。当李善德在岭南与长安间往返试运时,驿站快马累毙,沿途农户赋税加重。当他最终成功设计出“分枝植瓮”之法,等待他的却是同僚陷害与功绩掠夺。
马伯庸用荔枝这一微小切口,剖开了大唐天宝年间的溃烂肌理。一个帝国从上到下全部沉溺在纸醉金迷中。当唐玄宗纵情于霓裳羽衣曲,当杨贵妃笑啖岭南鲜荔时,杜甫正目睹着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人间惨剧。更可怕的是,这种奢靡已异化为某种制度性腐败:新科进士的曲江宴要连摆数日,奢华的烧尾宴食单上列满美味珍馐。正如书中主人公李善德最终看透的真相:所谓“荔枝使”的差事,不过是权力体系吞噬良知的一个缩影。从《礼记》“国奢则示之以俭”的古训,到当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雷霆之势,中华民族始终在与人性之欲进行着持久博弈。当下我们强调“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”,恰是对历史教训的智慧回应。
“爸爸,吃荔枝……”女儿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,望着女儿手中晶莹的荔枝果肉,我忽然想起书中岭南老农的一句话:“荔枝要现摘现吃,隔夜的就不是那个味道了。”这话语中蕴含的智慧,或许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:任何盛世滋味,若要以透支民力、败坏纲常为代价,终将腐坏成苦果。唯有常怀敬畏之心,让权力运行如岭南荔枝般经得起阳光曝晒,方能守住那份历久弥新之清甜。